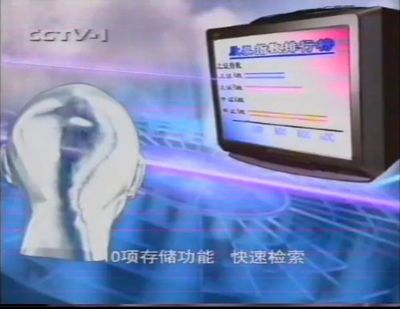客厅里只亮着一盏昏黄的落地灯,光线懒洋洋地铺在米色的沙发上。女人就陷在那片柔软里,身上搭着一条薄薄的针织毯。电视屏幕是这方空间里最活跃的光源,明明灭灭,映着她的侧脸。
节目是什么,她似乎并不真的关心。新闻主播字正腔圆地播报着远方的冲突与会议,广告里的人们笑得过于用力,推荐着某种能让人瞬间获得幸福感的零食。画面一帧帧流过,声音成了背景里一层模糊的、有规律的白噪音。她的视线落在屏幕上,又像是穿过了屏幕,落在更远、更空的地方。偶尔,她会无意识地拿起遥控器,换一个台,从一个喧闹跳进另一个喧闹,仿佛在寻找什么,又仿佛只是确认所有频道都一样乏味。
这一刻的客厅,像一个小小的、安静的茧。电视的声光成了茧壳,将她与屋外沉沉的夜色、与琐碎的生活暂时隔开。她也许在发呆,也许思绪正飘向白天未完成的工作、孩子明天的家长会、或是记忆中某个同样安静看电视的遥远下午。电视里的世界轰轰烈烈,爱恨情仇,生离死别;电视外的她,静止如一幅剪影,所有流动的思绪与情绪,都敛在那平静的凝视之下。
直到片尾曲响起,或是一个特别突兀的广告插播,她才仿佛被惊醒般,微微动一下,把滑落的毯子重新拉好。然后,继续看下去,或者,用遥控器轻轻一点,让整个客厅陷入一片黑暗与更深的寂静。那“啪”的一声轻响,是茧房合上的声音,也是这个寻常夜晚里,一个最寻常的句点。